这一次,做娄烨的观众吧
- A+
娄烨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导演里最被大众所低估的一位。

这种“被低估”的原因交织了几个不同层面。首先,他长期都被归类在独立导演里。至今为止,他有十部作品问世——而其中绝大多数的传播渠道都是盗版DVD。这就使他和“影迷圈”以外的观众距离比较遥远。
近20年前,当大放异彩的《苏州河》被美国《TIME》杂志选为2000年十佳电影之一,并已被一代文艺青年奉为圣经时,一般观众们还正在为《一声叹息》里的中国式婚外情长吁短叹。
而在国际上,娄烨无疑是内地最有才情的创作者之一。
从《紫蝴蝶》入围2013年戛纳主竞赛单元开始,他的作品就备受海外市场青睐,屡屡入围戛纳、柏林等国际A类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更三次被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最佳导演,外媒甚至称他为“中国的伯格曼”。不过,直到2014年,娄烨的上一部电影《推拿》拿到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摄影)并横扫六奖成为金马的最大赢家,普通观众才渐渐开始熟悉他。

《紫蝴蝶》
这种“能见度低”,当然和他拍的题材有一定关系。从《苏州河》开始,娄烨就在经历“片子没过审送影展—被惩罚禁拍—只能在国外拍片”的漫长轮回,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年。在第六代导演里,他为创作付了最大代价,却又最低调最不刻意——他的电影其实并没有什么匠气的“文艺片”姿态,尽管一直是用写实手法,但叙事冲突也很足够(像《浮城谜事》就是改编天涯论坛上一个“收拾贱男和小三”的狗血帖子),每部电影的故事性都并不弱。
而回顾娄烨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他会被低估,不只因为他“独立”,更因为他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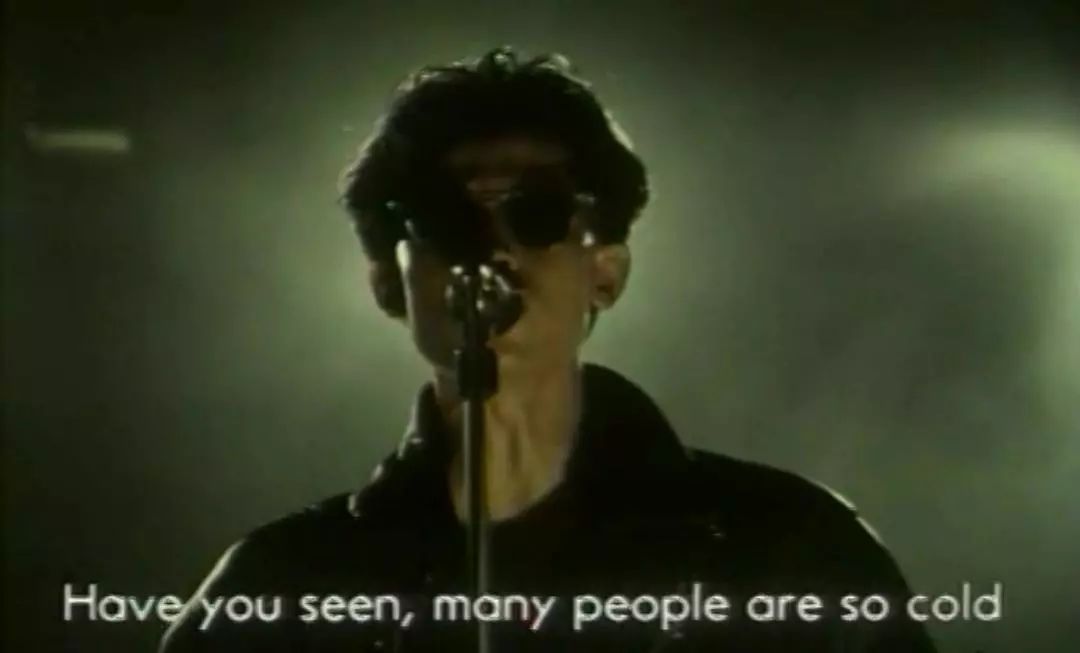
《周末情人》
早在国营制片厂还没倒闭的1990年代,娄烨的处女作《周末情人》虽然很像学生作业,但已初步有了当年的“青年作者”轮廓。后来《周末情人》一直没通过审查,他顺便又拍了一部很先锋很文艺的邪典片《危情少女》:叙事比较凌乱,但各种对表现主义的借鉴跟当时的香港B级片也算有一拼。两部不成熟的作品,让他完成了早期的摸索,到《苏州河》惊艳问世时,他的个人风格已基本确立。
包括被吐槽最多的“摄影太晃”等各种娄烨美学,都始于《苏州河》。如今回过头去看,人们可能更能意识到,当年那部电影里的影像表达是很前卫的。

《苏州河》
每个导演都有一套营造“电影感”的方式,而手持摄影、跳切和表情特写就是娄烨把控和呈现情绪的独特标签,所以他擅于拍混乱、游离与不确定:那些在“秩序”以外无法被定义被说明的个人情感和状态。
也恰恰指向当代中国的常态。
因边缘而独立得自由
娄烨电影既有影像上的前卫,也有观念上的超前。
爱情不用多说,他电影裡的一切都和爱情有关——除了爱情本身。
《苏州河》里,爱情一旦眼见为实就只能选择离开。《颐和园》是太轰轰烈烈的一拍两散让当事人怎么也缓不过来。到了《花》,女主角发现忠于爱情和身体会更失去自我。而《浮城谜事》虽然小三小四齐上阵,但男主角最爱的人根本还没出现(娄烨自己说的)。

《浮城谜事》
说到底,爱情关乎的是选择用哪种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反正城市永远是游移的,现实永远是压抑的,人也永远是边缘的。
很多人说娄烨是中国最会拍“女性”的导演(比如《颐和园》里的余虹就绝对让人过目不忘)。但与其说他能精准拿捏的是“女性气质”,不如说是“边缘气质”——或者应该说正因为边缘,所以才显得女性。如果你以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讨论性别议题时,女性已经不再弱势,自然大错特错。这也正是为什么娄烨电影总给人感觉女性是主体,其实他只是一直在拍边缘的个体。

在世纪之交高速发展的上海,他的镜头却对准遍佈肮脏垃圾的苏州河,底层男女在别人的荒诞故事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颐和园》的噱头虽然是性和政治,但主角其实是跟不上星辰变换飞速向前的80年代自由主义牺牲者。时代不负责为个体疗伤,余虹也就寸步难行。
到了《春风沉醉的夜晚》,镜头还是晃得厉害,却又拍得那么美。这部十年前的同性题材作品,至今为止都是中国大陆最富诗意的LGBT电影,而且能用高度文学化的方式去切入“性少数群体”的导演,华语世界也只有娄烨。

《春风沉醉的夜晚》
而《花》里的异国他乡处境,有娄烨对“流放”和“回归”的个人思考。因为题材和影像上的边缘,所以多年来他只能“独立”,却也因而获得了自由。当然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多数观众根本不了解他。所以《浮城谜事》就像一部过渡期的调试之作,里面有他前面很多部作品的影子。
最终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推拿》,关注的还是边缘的盲人群体——不过,盲人的世界一样有秩序,唯一没被体制同化的男主角小马则是个自由主义者。

《推拿》
娄烨本人其实也是中国最有自由主义气质的导演。
首先他始终在追求一种自由的电影语言。尽管有些观众会觉得视觉不适,但他大量使用的手持摄影推拉变焦又确实最适合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浮城谜事》里郝蕾跟踪老公的心情)以及有强烈现实质感的场景(比如警察去夜店扫黄)。其次,因为他的主角永远处在边缘的位置,所以他们势必要不断面对自由的问题。
但自由主义的困境,其实又是共通的,那是不分主流与边缘的“人最基本的困境”——这也是为何娄烨的电影总会涉及到性、暴力、边缘者、弱势者。我从来不觉得他拍那些是为了独立而独立,如果一定要说他身上有某种反抗的姿态,可能也只是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每个人想要自由地活着,都是不容易的。
最个人又最当代
而对中国观众来说,可能当下也是最适合去关注与理解娄烨的时刻。
中国社会从未像眼下这样以个体为中心,尤其在都市,对于个体化、私利化的追求已经是非常主流的意识。而娄烨电影所在意的,恰恰永远是个人。
他不像很多导演那样动不动就要把历史和现实打通,用个人故事升华出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正相反的是,即使他在拍时代的大开大合,落脚点都永远是最个人、最私密的困境——他在意的是在体验过冲上云霄后的余虹要怎么处理身体停不下来的惯性;留学法国的中国女生“花”要怎么在身份阶级都不匹配的情欲裡自处——很多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了政治,但娄烨并不太关心那些,他只是关心“人”:一个最普通微小边缘的人,如何在今天这样失序的当代社会活下去。
能把个人的痛说清楚,才能书写出时代的痛脚。

《推拿》
底层的痛、同妻的痛、盲人的痛、被背叛被羞辱的痛、被暴力以待的痛、乃至是被深爱的痛,所有这些属于个体的痛,没有哪个导演讲得比娄烨更用心。它们全部都是当代生活里的悲伤切片,组合在一起,就拼出了中国社会的面目。
也因为是个人的,所以最能让观众共情和代入。
其实进入娄烨的电影一点都不困难,你很容易从他那些角色身上辨认出属于自己的孤独、焦虑无力乃至格格不入,毕竟个人能经历的苦其实都差不多,大家在这个时代里所遇到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正如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每一个角色都被囿于自我的困境中,被利用,被陷害,被追捕,被迫深陷泥潭,被身份认同所困扰,在有限的篇幅里,娄烨精准地描绘出每个角色的性格、动机和状态,织就一张错综复杂的都市群像网,也让观众很容易地对他们产生共情。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另一方面,娄烨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和驾驭能力是极具天分的。他不像很多第六代导演那样有野心从历史书写到未来,他所瞄准的就是当代。
或许因为当代中国已足够魔幻足够“反类型”,所以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谈到自己的最新作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娄烨坦言:“中国的社会空间已经不可能找到什么现成的‘类型’去表现了”——不是因为想要用“反类型”的超前姿态去创作,而是因为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太“反类型”、太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你依然能感受到娄烨电影中的“当代感”。
故事由一宗坠楼案引入,时间纵深跨越三十年。从一个逐渐陷入案件疑云的小警察,引出一张横跨三十年的人物脉络网,又辐射出这背后整个野蛮生长的时代。
虽然在他的镜头里,无论哪个城市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灰色地带,但城市空间变动与人物状态的关系,他处理得总是恰如其分:个人的问题,可能带出家庭伦理问题,私事又牵动更大范围的社会写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同样是在延续这样的路线,且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也令人怀有更多期待。
曾经专门把娄烨电影找来当情色片看的观众,大概如今已经能从他的电影里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而我更一直觉得,他也不是很在意被公众低估,只是愿意一直在前面静静等待有缘人跟上他的节奏。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终于准备好,成为娄烨的观众了吧。





















